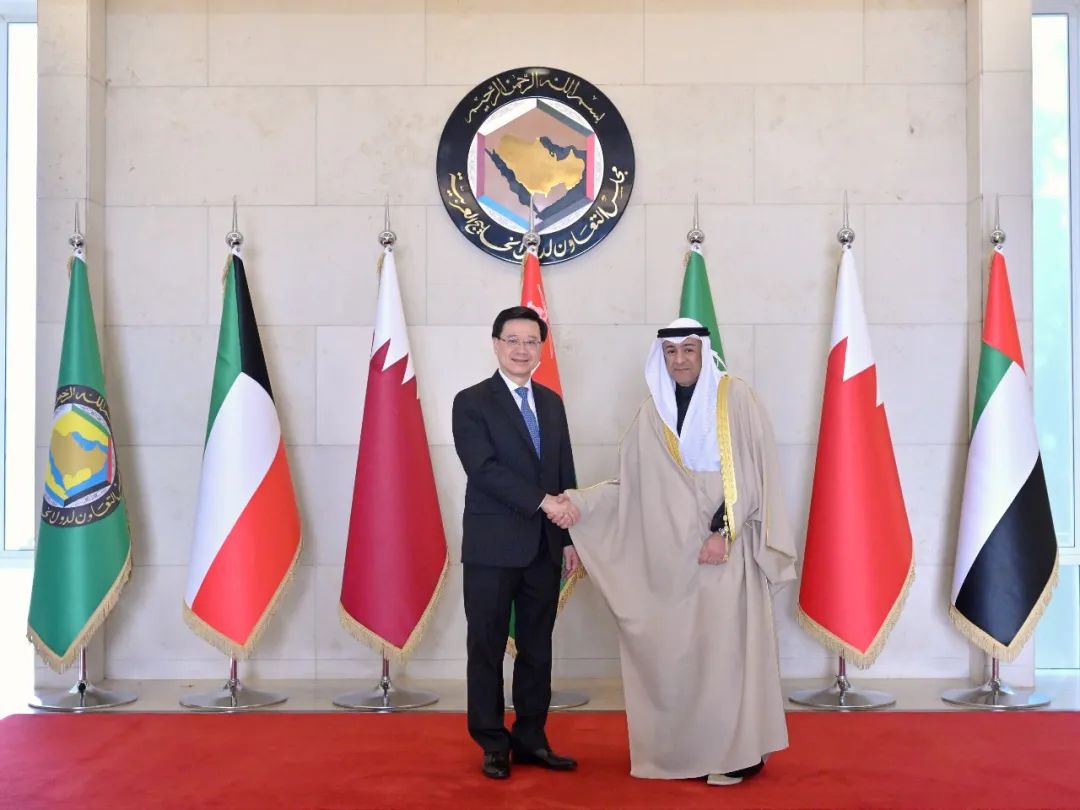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思考國際金融中心的演變需要拉到一個更長的歷史尺度來尋找時代所處的坐標。現代全球化的進程大致可以分為如下幾個階段:十九世紀末到一戰之前是全球化第一波浪潮,建立在英國霸權和西方列強擴張的基礎之上;從一戰開始到二戰結束,全球化的政治基礎走向了崩潰和重構;二戰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治理體系成為了全球秩序的基礎,第三世界國家積極尋求獨立自主發展;冷戰期間,美蘇爭霸和兩大陣營的對抗是一個鬥而不破的過程,這一階段新一輪的全球化開始孕育;冷戰結束之後,國際體系進入一超多強結構,新一輪全球化向縱深發展,體現在全球供應鏈崛起、產品內分工深化與金融全球化擴張。
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很大程度上也得益於這一波全球化浪潮;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世界已進入新一輪全球化大變局,全球化的地緣政治基礎和在主要大國的國內政治基礎都面臨重大挑戰,全球化面臨重組的壓力。
從大歷史的角度看,地緣政治與安全格局在國際金融中心的更叠演變過程中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十七世紀到十八世紀,阿姆斯特丹是最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但隨著十八世紀末法國入侵荷蘭,阿姆斯特丹走向衰落。英國和法國,特別是英國,替代了荷蘭的國際金融主導權。
十九世紀國際金融中心演變的主線是倫敦和巴黎的競爭。由於法國在拿破侖戰爭、普法戰爭中陸續失敗,巴黎與倫敦的差距日益擴大,走向相對衰落。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倫敦是主導性的全球金融中心。後來隨著美國的崛起,經歷了冷戰及其後的新一輪全球化,紐約替代倫敦成為了最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而倫敦得益於離岸美元市場的發展,依然保持著重要地位,形成紐約—倫敦雙中心的架構。

倫敦金融城
(圖源:英國獨立報)
1980年代以來,隨著新一輪全球化推進,亞洲新興經濟體崛起,逐漸形成了東京、香港、新加坡等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蓬勃發展的新格局。
在全球化大變局的背景下,經濟金融政策不僅要考慮經濟理性和發展的邏輯,也要充分考慮地緣政治和安全的邏輯,需要統籌發展與安全。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不可能脫離國家金融實力和金融安全的宏觀基礎。國家金融實力取決於很多維度,包括實體經濟規模、發展水平和開放程度,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深度、廣度和韌性,外交關系網絡、軍事力量和輻射範圍,以及治理體系的有效性等。
從體量上看,2020年,中國GDP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占到全球GDP的18%,貿易占比是全球的12%,已經超過美國。然而,人民幣占全球外匯儲備比例只有約2.3%。美國雖然只占有11%的全球貿易,但是美元占到全球外匯儲備的60%以上。當前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本質上依然是一個金字塔結構,是在美元和美國金融霸權主導下的高度不對稱、不均等體系。
國際金融博弈有很多層次,既有雙邊關系上的博弈,包括金融製裁和援助,也有多邊結構上的博弈,包括通過主導多邊秩序、規則來塑造體系運作,還有意識形態上的博弈,包括對金融監管理念、改革思潮的影響等。當前,在所有這些層次上,國際金融政治化、武器化的趨勢都越來越明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關註金融安全。
金融安全代表著一國金融體系抵禦內外部沖擊的能力,代表著金融主權相對處於一個沒有危險和不受威脅的狀態,國家利益處於免受金融手段和渠道威脅的狀態。金融安全是國家安全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二十大報告充分強調了統籌發展與安全的重要性。我們在思考如何鞏固和增強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時,需要有歷史觀、大局觀和角色觀。從統籌發展與安全的大局出發,充分把握香港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的獨特戰略地位和角色。一方面,香港應進一步發揮「雙循環」超級聯系人的作用,在全球產業鏈重組、地緣政治變局、產業技術革新的背景下,聚焦 「一帶一路」,引導金融市場更好地配合區域產業鏈、供應鏈的重組和發展。另一方面,香港應進一步融入內循環,推動與內地金融市場的互聯互通,同時也推動金融業更好服務本土實體經濟和創新。此外,香港在建設與國際接軌且安全可控的金融基礎設施方面,應當發揮引領作用,包括充分推動金融科技及金融監管科技創新,把握數字貨幣和支付技術革命的機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增強涉外金融基礎設施的自主安全可控水平。

圖源:AFP/Getty Images
面對全球化大變局的沖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需要保持對地緣政治博弈和金融安全博弈的充分敏感性。正如《孫子兵法》所言,「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最理想的情況是事前化解風險,但也需要進一步建設金融安全的事中、事後反應機製,做好應對極端狀況的準備。
(本文內容原載於《紫荊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