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 2024.3.14
一般意義上的“中國通”是指別國、特別是西方學界(政策界)對中國情況比較熟悉的專家學者,也被稱為“漢學家”“海外中國問題專家”,他們所從事的研究 ,我們稱之為海外中國學、海外漢學等,涉及政治學、人類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等許多領域。 由於中美關係是中國外交的基礎性關係,美國的「中國通」更為受到中國的關注。 這些「中國通」在學術和政策上的影響力大,多數曾在美國決策體系中任職,他們的對華觀點往往能夠影響本國對華決策以及對他國民眾對中國情況的感知,具有較高的 可信度和權威性,也受到中國決策層到學界乃至一般民眾的關注。
如今,在美國對華戰略中,中國是美國「戰略競爭者」的整體判斷已經定調。 可以預見,「中國通」將在具體對華戰略制定中發揮更大作用,因此,研究其共同特徵和變化,對於研判未來中美關係走向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聚焦在政治和外交領域,分析美國的「中國通」所發生的變化。
從美國的「中國通」說起
2015年1月,中國的外交學院召開了“美國知華派與未來的中美關係學術研討會”,根據“對美政策影響力、學術影響力和社會影響力”三大指標測算,包括了 大衛·蘭普頓、沈大偉、金駿遠、李成和李侃如等著名對華研究學者,這些學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都是美國對華研究的領軍人物,具有相當代表性。

美國知華派排名(圖源:外交學院「美國知華派專家評估計畫小組」報告)
(一)從美國「中國通」的學科分佈看
美國大學的政治學一般為5-7個細分方向,包括:1)政治哲學;2)美國政治;3)比較政治;4)國際關係;5)政治經濟學(有時與經濟學系共享) ;6)戰略與安全研究;7)方法論。 「中國通」學者普遍歸屬在比較政治、策略與安全研究、國際關係三個方向,彼此之間有交叉重疊。
「中國通」在美國構成了東亞研究和中國研究的學術共同體,彼此之間具有學脈譜系的傳承關係,從費正清、鮑大可到黎安友、蘭普頓、沈大偉、李侃如、謝淑麗、白邦瑞, 再到新一代的傅泰林、蔡斯、毛雪峰、白潔曦、吳志遠、麥可貝克利、江泰樂等。 美國的「中國通」整體形成了接續有序的人才梯隊生態,能夠持續輸出對華觀點和研究成果,成為不可忽視的戰略思想力量。

大衛蘭普頓在「2023年香港中美關係論壇」的特別對話活動中接受了《中美聚焦》駐美編輯馬克(Marc)的採訪(圖源:China-US Focus)
(二)從機構分佈來看
遍佈大學和智庫,並且呈現從大學轉移到智庫的趨勢
大學機構和社會智庫在美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決策中發揮了多重積極功效,特別是在對華政策方面,發揮了以下作用:
1. 美國對華重大戰略思想與新興概念的創新源頭;
2. 美國中國學研究成果的轉化應用場所;
3. 多元戰略思想交鋒爭論的辯論場;
4. 為軍政退休退休、政黨輪替涵養戰略思想人才的「蓄水池」;
5. 美國講「中國故事」(更多是中國「威脅論」「崩潰論」「衰退論」)的戰略輿論力量;
6. 世界各種勢力前往美國華盛頓表達對中國態度的載體平台,往往推動了中國內外部問題的國際化、複雜化、污名化(如南海、人權、邊境衝突等)。
1.大學中既包括政治及國際事務學院,也包括掛靠大學設立的智庫
比較著名的國際事務和政治學院包括了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問題研究院、普林斯頓大學伍德威爾遜國際事務學院、哥倫比亞大學國際公共事務學院、喬治城大學沃爾什外交學院 、美國海軍學院等。 有實力的大學也會聚焦國際關係和戰略安全成立大學智庫,比較有名的有哈佛大學的貝爾弗國際事務研究院、麻省理工學院的國際事務研究院(與政治系的安全項目有重疊)、 史丹佛大學的胡佛戰爭與和平研究所、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喬治城大學新興科技與國家安全研究所等大學智庫。
2.社會化智庫的策略角色更加突出
美國的社會化智庫體系高度發達,一般以非營利獨立法人的形式存在,既相互充分競爭,又有所分工專長,在對華決策中具有重要份量,成為美國國家安全體系(國務院、國家安全委員會 、國防部、中情局等)對華開展外交攻勢的高端人才儲備基地。 比較代表的有蘭德公司、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所(CSIS),布魯金斯學會、卡內基和平研究所、新美國安全研究中心、2049研究所、哈德遜研究所、傳統基金會 以及卡特研究所等。 這些智庫的資金來源,既有政府委託項目,也有社會捐贈,也包括自身項目獲利,整體上實現了良性的「自我造血式」發展。
美國「中國通」的共同特徵
成為美國的“中國通”,一般應有三個重大特徵:
(一)首先是中國問題專家
從中國具體領域問題研究進而成為中美關係的專家,其中美關係的研究具有區域國別研究的實證基礎。
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具有濃厚的區域國別研究的實證基礎,更加重視事實基礎上的邏輯演繹和結論觀點,較多使用田野調查、案例研究、開源資訊分析以及後來興起的定量工具。 也就是說,美國「中國通」的中美關係研究往往建立在對中國問題的堅實基礎上,從中國問題到中美關係的遞進發展次序。
美國的「中國通」往往在碩、博士階段就開始掌握漢語,並選定中國某個特定領域的問題進行研究,如軍事安全、軍事科技、對外衝突、外交行為、經濟政策、精英政治、抗爭政治等領域進行了長期的追蹤研究,成為了中國特定領域的專家,建構個人初期的學術聲譽。 伴隨著學術累積和學術職位的穩定,逐漸參與對華公共政策的討論、決策顧問諮詢。 一部分大學教授和智庫學者,會透過公開發表評論、學術文章和專著來系統性地闡述其思想,也有一部分透過「旋轉門」機制進入美國國家安全體系,從學入仕,擔任國防部、國務院等 負責中國和東亞事務的官員,或成為高級政治領導的諮詢幕僚,從而將學術上的思想和理念付諸實踐。

美國國防部五角大廈(圖源:AP)
(二)具有美國對外政策方面的影響力
其所提出的戰略思想或理念,能夠影響甚至主導美國一段時期或是某一些高階領導人的對華政策,從而為中美的決策層所關注。
沒有政策影響力的“中國研究”學者很難稱之為“中國通”,如哈佛大學政治定量方向的Gary King教授,近年來運用中國公開數據發表了多篇政治學頂刊《美國政治學評論》 ,是該刊物發表關於中國話題的數量之最,但是無論是其本人或是外界,都未曾將其稱之為「中國通」。 因此,要成為美國的「中國通」:一是與政策問題保持著密切距離,從自身研究特長出發,持續關注中國發展態勢與雙邊關係,及時進行戰略研判、觀點輸出、公開發聲、諮政建言 等活動。 二是與政策決策機構保持密切的距離,如透過「旋轉門」機制(學者與國家安全體系的人員交流)出任國務院、國防部、中情局、眾議院委員會職位,或是成為政治領導或機構的諮詢 顧問,參加國會聽證會作證,圍繞中國發展和雙邊關係寫作報告、答疑質詢。 如美中經濟與安全評估委員會(美國政府於2000年10月通過國會授權設立,主要負責監督和調查中美之間的國家安全和貿易問題。成員由兩黨國會議員所任命,每年發布年度報告 ,被認為是美國白宮、國會制定對華政策的重要指南),其報告的撰寫成員多數來自美國國內高校和智庫的頂尖中國問題專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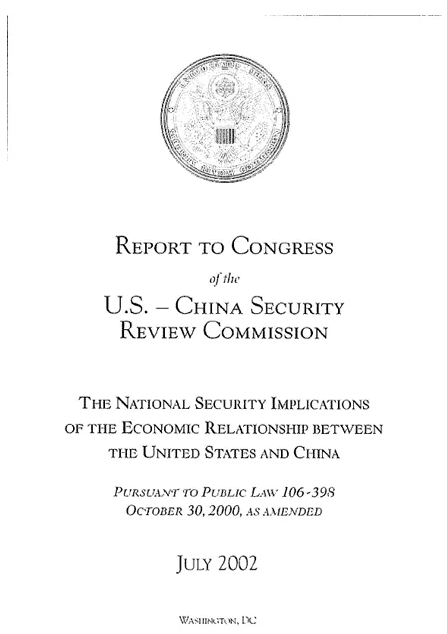
《美中經濟與安全委員會2022年度報告》,該委員會向美國國會提交的首份年度報告(圖源:美中經濟與安全委員會官方網站)
(三)與中國各階層保持廣泛的接觸
與中國各階層(至少對美關係機構和研究機構、學者)保持著廣泛的接觸,能夠較為深刻的理解中國的文化和態度。
老一代「接觸派」的「中國通」往往在青年時期就透過到中國訪問交流、學習漢語、旅行、田野調查等多種方式與中國建立了親密的聯繫。 甚至許多「中國通」與中國人結成了婚姻,如費正清、黎安友、Hal Brands,他們對中國有著較一般美國學者更為深刻的理解和親近,對中國文化和人民抱著更為友好和 客觀的立場。 他們也會透過招收中國學生和訪問學者、與中國政府人員的接觸交流,與中國方面保持了較為直接和真實的接觸,因此,他們能夠以更為冷靜客觀的視角觀察中國的世紀發展情況。

費正清(1907-1997)美國漢學家、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創辦人。
圖為在北京四合院舉行婚禮的費正清費慰梅夫婦(圖片來源:央視網)
美國「中國通」群體的一些變化
1.美國的「中國通」群體面臨遏制派崛起、接觸派壓制的結構性壓力
近些年,在中美戰略關係日益緊張的情況,對華相對客觀友好的接觸派「中國通」(如蘭普頓)被壓制,主張對華強硬的「遏制派」學者崛起,並逐漸主導 了美國對華政策的話語權,與美國對華政策的強硬形成了“思想—政策共振”,許多不理智、不客觀、對抗性的話語進入了雙邊的對話論戰。 (在相關研究中可見,David M. McCourt(2022)發表在《安全研究》上的“Knowledge Communities in US Foreign Policy Making: The American China Field and the End of Engagement with the PRC”《美國中國學研究與 接觸派的終結》)
2.美國新一代在大學生存的「中國研究」學者,不自覺地與現實的中國拉開了距離
為了能夠在高校的終身教職考核中通過,也不得不更加傾向於採用定量研究,利用更短時間“衝刺”頂刊,不可避免地也帶來了“在數據中造論文”“在黑板上 研究中國」的問題,造成了這些學者很難(甚至無意於)深刻理解中國的現實政策問題,也難以了解政策和問題背後的隱性訊息。 這不僅受限於激烈的晉升考核壓力、美國政治學科的整體定量轉向影響,也因為中美關係緊張、美國學者在中國訪談調查的難度加大的原因。 我們可以初步觀察到,美國對華研究逐步出現了大學「學院派」和智庫「政策派」的分野,智庫「政策派」的學者較為正面的現象。 這項學術與政策的分離,間接上也使得美國對華政策研究缺乏了歷史穿透力和理論說服力,往往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片面感、短視感、局限感, 缺少了宏大的整體性視角。
3.「中國通」專家學者逐漸往中國的軍事戰略和國家安全領域集中
相較於老一代「中國通」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議題的關注,新一代「中國通」似乎更青睞軍事安全,選題時往往更關注中國的軍事現代化、軍事科技、戰略威懾等 傳統戰略與安全領域,逐漸成為美國新一代「中國研究」的顯學領域。 筆者所接觸的一些在讀美國博士,發現他們更傾向研究中國的軍事與安全主題。 這項轉向,一方面是因為美國高度關注中國的軍事發展、話題熱度高、國防部和各界的「慷慨」資助,適用範圍廣,不少博士也具有軍事背景;另一方面,筆者猜測,也是 因為該領域資料可得性差(有人詼諧地稱之為「政治學定量霸權的一塊淨土」),更強調基於開源資訊的分析,對定量和一手調查訪談的要求相對低一些,更適宜政策導向的研究。
新一代「中國通」不約而同地向軍事戰略與安全領域的轉向聚焦,既凸顯了今後中美兩國關係中對抗性因素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可能意味著主導今後一段長週期的新「中國 通」們對中國的態度更加客觀甚至「疏離」。 他們是將中國視為一個冷靜客觀分析的對象國,而非試圖理解其歷史和文化內涵、注入個人情感和學術理想的田野國家。 在這一背景下,許多“中國通”已不再“通”,他們更加專注於中國的某個具體問題。 例如,目前已經擔任美國國防部負責中國事務的副助理國防部長邁克爾·蔡斯(Michael S. Chase先後經歷美國海軍戰爭學院、蘭德公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高級問題研究院),其 專長在於研究中國海上安全及軍事現代化,對中國軍隊的改革、海上軍事力量等問題具有較好的研究積累,但是很難看出其對中國其它領域的關注和興趣。 相較於其導師蘭普頓教授對中國的整體性理解和換位思考,查斯對中國的態度更加專注、客觀、疏離。 因此,主導未來中美關係戰略思想所創造的「中國通」們向軍事安全領域的轉向趨勢,將會間接影響今後中美兩國關係的宏觀視角和微觀操作的態度。

邁克爾·蔡斯於 2021 年 5 月在美國防務學院的校園訪問(圖源:DVIDS)
美國的「中國通」真的「通中國」嗎?
美國的「中國通」群體是中國開展對美關係,甚至是審視自身戰略決策所不可忽視的戰略思想群體,他們一定程度上也發揮了給中國「照鏡子」「扯袖子」的外部「吹哨者」作用。 同時,他們也是中國開展對美「二軌外交」的重要橋樑和管道,特別是在中美關係面臨困難和危機處置時期,當官方通訊管道受阻,或許中美雙方的專家學者將發揮靈活柔性的 連結作用,有利於中美關係裝上「避震器」。 隨著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美國戰略界對「中國通」群體更是有所批評,認為他們沒有預測中國對美國日益嚴峻的戰略挑戰。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哈爾·布蘭茲( Hal Brands)在彭博社發表專欄,把觀察中國的專家分為「中國通」和戰略學者兩類。 他認為在冷戰後認識並且宏觀把握來自中國的挑戰方面,大國戰略專家往往對中國的未來意圖預測得更準確,許多最具前瞻性的文章都不是出自“中國通”之手。 面對中國的崛起和挑戰,「中國通」和知華派往往都沒有做出正確的預測,而是那些沒有專門鑽研中國的大戰略專家準確預測到了中國崛起帶來的戰略挑戰。
大國戰略專家大部分不是“中國通”,他們通常不通漢語,也沒有在中國的學習生活經驗。 他們更多是把中國看作是一個「全球競爭對手」而非一個歷史悠久的獨特文明。 相較之下,精通漢語、熟悉中國文化、掌握和中國政治階層的聯繫渠道且有許多中國社會關係的“中國通”,更為精確地把握中國的政治、歷史和戰略,卻無法預測中國的 未來。 針對這樣的批評,或許我們可以理解為這是對美國的「中國通」所提出的更高要求,但是我們無法否認美國的「中國通」在影響美國戰略決策、加強中美雙邊交流理解、避免 戰略誤判所扮演的巨大角色。 他們或紮根大學著述育人、或遊走智庫「兜售」思想、出仕入學、廟堂民間,成就了美國一道獨特的知識分子群像。
如果更進一步觀察,我們可以發現,由於多方面原因,美國的「中國通」或許也很難「通中國」了:
1. 海外中國學研究進入更細分的專業化分工
海外中國學研究會進入更細分的專業化分工,“中國通”更準確地說是“通曉中國某個具體領域”,如軍事安全、經濟改革、政治體制等。 海外中國學的學術建構已經較成規模,為了因應日益激烈化的研究競爭,專注細分領域成為海外中國學發展的必然階段,老一輩基於宏觀視野總體把握的「中國通」已逐漸被具體領域 的中國問題專家所接替,「中國通」已難以「通中國」。
2. 學院派學術研究和智庫派政策研究的分野將繼續拉大
學院派學術研究和智庫派政策研究的分野仍將繼續拉大。 我們可以看見一個初步趨勢:美國從大學學者身分進入國家安全決策體系任職的現像日益減少,轉而由大量在智庫工作的政策分析專家進入「旋轉門」。 也鮮有退休官員進入大學擔任教職,且常擔任高校智庫的高級研究人員,而非重返學術道路。 美國戰略與安全領域的學術與政策在冷戰後期已發生較大分野,以致於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一代戰略大師從學術界的退出,這一學術與政策的隔閡趨勢仍將在 海外中國學中繼續發生。
3. 海外中國學逐漸轉向更抽象的學術理論建構
隨著政治學學科的發展日益成熟,海外中國學要成之為學,也必然會擺脫接近情報分析或新聞報導式的描述性分析,轉而走向更具有高度抽象特徵的理論建構。 海外中國學不再局限為區域和國別研究,既強調對政治學主流理論和比較政治的最新成果的應用,同時也強調對主流政治理論的貢獻。
結 語
美國的「中國通」和中國的「美國通」是未來中美關係的晴雨表、體溫計、連接橋、避震器,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 習近平總書記說,中美關係的未來在青年,我們也應當積極歡迎新一代美國學子在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形成的青年時期,到中國親自感受、與中國人交朋友,或許這更能奠定 中美未來關係的整體走向。 與之相對應,中國新世代學派也應當繼承和發揚老一代學人的學術傳統,成為新一代中國的「美國通」。 後續文章將圍繞「中國如何產生『美國通』」繼續分析為什麼當前我們還很難培育起與美國「中國通」相比肩的「美國通」。
本文作者
梅陽: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員。
*原創聲明:本文版權歸微信訂閱號碼「大灣區評論」所有,未經允許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轉載、複製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本文部分或全部內容,侵權必定。 公眾號授權事宜請直接於文章下方留言,其他授權事宜請聯絡IIA-paper@cuhk.edu.cn。
GBA Review 新傳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