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據美國航天局今年1月中旬發布的報告顯示,2022年與2015年並列為自1880年有氣象記錄以來的第五熱的年份。 2022年全球氣溫比19世紀末的平均氣溫高約1.11℃。數據顯示,人類活動導致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在2020年因新冠疫情短暫下降後,已開始反彈,全球氣候變暖趨勢不容樂觀。本報告認為,全球氣候治理朝著“脫實向虛”的方向發展。出現這種狀態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氣候治理的“政治化”,體現在西方綠色力量在全球氣候治理和談判中發揮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氣候治理的“道德化”,體現在氣候議題將更加關注“公正轉型”與“下一代”等問題。
導讀· 2023.02.02
據美國航天局今年1月中旬發布的報告顯示,2022年與2015年並列為自1880年有氣象記錄以來的第五熱的年份。 2022年全球氣溫比19世紀末的平均氣溫高約1.11℃。數據顯示,人類活動導致的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在2020年因新冠疫情短暫下降後,已開始反彈,全球氣候變暖趨勢不容樂觀。
面對持續惡化的氣候問題,去年11月20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沙姆沙伊赫大會(COP27)在全球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中落幕,峰會上各國達成了有限共識,但無助於全球溫控目標的達成。會後被廣泛宣揚的“損失與損害”基金的確立,實質上僅僅是形式,暫無任何實際行動方案。
本報告認為,全球氣候治理朝著“脫實向虛”的方向發展。出現這種狀態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是氣候治理的“政治化”,體現在西方綠色力量在全球氣候治理和談判中發揮的作用;另一方面是氣候治理的“道德化”,體現在氣候議題將更加關注“公正轉型”與“下一代”等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氣候外交要“虛實並舉”,在明確不把氣候問題政治化的原則下,在“實”的氣候外交中充分全面地把中國的故事數據化和案例化;而在“虛”的氣候外交中可以利用道家和儒家倫理對接西方“道德化”,突出道家和儒家倫理中“天人合一”的普世價值,以氣候問題為抓手擺脫西方對中國價值觀的封鎖和孤立。
實質上的倒退
在埃及沙姆沙伊赫舉辦的第27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以下簡稱COP27)於2022年11月20日達成所謂“歷史性”協議,使這場被譽為“屬於非洲的COP”結果令人失望——談判達成的協議不僅止步不前,還有倒退的跡象。特別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兩項核心訴求均有倒退跡象,包括更進一步的全球溫室氣體減排承諾和氣候資金的兌現[1]。

在埃及舉辦的第27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
(圖源:路透社)
首先,1.5℃溫控難以兌現。
峰會達成的最後決議文件稱,到2030年,將全球變暖控制在比工業化前水平高1.5℃的範圍內,需要“快速、深入和持續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然而當前全球平均氣溫已經至少上升了1.1℃。聯合國最近的一份報告得出結論稱,按照目前的政策和進度,到2100年全球氣溫將上升2.7℃[2]。
儘管各國都認識到減排的緊迫性,但如果比較峰會前後兩屆的草案文本,就可見減排計劃進展極為有限。這份決議文件與格拉斯哥氣候協定的文本相比,有對能源部分的表述相當於一進一退,在“逐步減少”(phase-down)的表述上變為“逐步淘汰”(phase-out)未採用捕集與封存措施的煤電,這是進一步;但在逐步淘汰化石燃料補貼中增加了一個“合理說明(rationalize)” 低效的化石能源補貼,也是峰會向石油生產國的妥協,這又退了一步。
因俄烏戰爭引起的全球能源危機,讓能源轉型步履蹣跚。部分西方國家因為缺乏便宜的天然氣,轉向以煤炭與石油補足能源缺口。雖然COP26上曾大力呼籲停止對煤炭行業的公共投資,但2021年全球在化石能源產品的公共投資比2020年多出一倍(見圖1)。與化石能源有直接關聯的COP27參會者,從2021年的503人上升到636人,這數字僅次於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代表團,被媒體稱為“化石產業遊說團體在COP的爆炸性增長”[3]。

圖1:82個經濟體主要能源產品(煤炭、電力、天然氣、石油)的公共投資及石油價格波動趨勢
(圖源:OECD)
其次,氣候資金援助難以兌現。
2009年,發達國家同意到2020年底前每年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0億美元的氣候行動資助。後來,該承諾也成了2015年《巴黎協定》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根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21年公佈的數據顯示,《巴黎協定》簽訂以來,發達國家拿出的氣候援助金額一直在增長,但都沒有達到1000億美元的承諾,而且漲幅逐年減小,2019年僅比前一年增長了2%。發達國家每年氣候援助從2013年的524億美元增長到了2019年的796億美元,與1000億美元的目標還差超20%的距離(如圖2)。然而,即便這1000億美元的承諾得到兌現,也只是欠發達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所需資金的一小部分,按照當前發達國家的履約情況來看,幾乎不可能再進一步增加援助資金了。

圖2:2013-2019年,發達國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氣候資金(十億美元)
(圖源:OECD)
形式上的“進步”
首先,沒有實施方案的“損失和損害”基金 (“Loss and Damage” Fund)只是形式上的進展。
非洲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僅佔全球不到4%,卻極易受到氣候危機的影響[4]。同樣的情況對南美洲和太平洋島國來說是一樣的。從道義上講,這些中低收入國家不應該為已經實現了工業化的高收入國家承擔氣候風險和威脅。早在1991年,太平洋島國瓦努阿圖(Vanuatu)首次提出設立國際保險基金的想法,以補償小島嶼發展中國家因海平面上升所造成的影響。自那以後,發展中國家在氣候談判中不斷施壓,但是一直沒有進展。就在COP27上,這項訴求有了形式上的“進展”。
COP27達成了“損失和損害”基金以補償發展中國家因氣候變化造成的損失和損害。大會稱“這是朝著正確方向邁出的一步,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的鼓舞和支持”。但具體可執行方案,即賠償如何執行被推遲到2023年的COP28上討論。至於資金流有多大、誰支付,以及最關鍵問題——誰來控制和管理這些資金,各方均沒有達成一致,聲明也未涉及。另外,由於“損失與損害”尚無明確的官方定義,因此用於支持此項議題的資金和用於支持人道主義援助的資金之間也無明顯界限:援助主要是對事件的反應,且更聚焦資金缺口並確保專項資金不會被挪用或貼上其他標籤;而處理損失與損害不僅涵蓋快速響應,也包括應急基金和保險等主動措施,重點關注對於脆弱社區的資源調動和支持[5]。定義的缺失所造成的影響之一就是在當前公眾可及的官方財政信息中,難以對“損失和損害”的資金進行明確的標註和說明,進而使得民眾或者關注此議題的機構和組織難以用相關數據和案例進行深入分析和決議。換句話說,有關“損失和損害”基金執行和監管基本難以落實。

COP27同意設立“損失和損害”基金
(圖源:美聯社)
其次,首個關於“公正轉型”邊會,各國在議題上存在較大分歧。
這次大會上,歐盟委員會和國際勞工組織(ILO)還共同主辦了聯合國年度氣候大會上的首個“公正轉型”邊會(Just Transition),首次成立了“公正轉型工作計劃”(Just Transition Work programme)。峰會決議當日也表態對公正轉型的支持,支持發展中國家在能源轉型與產業轉型的路上,同時顧及社會福利保障、社會溝通等面向,並同意每年召開部長圓桌會議專門就該議題進行討論。不過,在峰會決議文本中未納入“勞動權益”與“人權”,說明各國在“公正轉型”議題上存在較大分歧,但“公正轉型”的加入進一步提高了峰會的道德性,加強了ILO等組織的道德話語權。
此外,本次大會設立了首個關於“兒童和青年”的邊會。
COP27首次為青年和兒童開辦邊會,讓兒童和青年發出自己的聲音,以增強他們參與氣候行動的能力。邊會由青年組織和運營,自主成立工作組並舉辦活動。這進一步凸顯了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道德製高點,即為了下一代人的利益。但是氣候問題的“道德化”從氣候談判的角度來看並不意味著進步。從短期來看,這種“道德化”更多會停留在輿論層面,不可避免地流於形式;長期來看,氣候問題的道德化必然導致其政治化,並很可能演變成全球尺度的“左右之爭”,一邊是代表既得利益的保守主義,另一邊則是代表新晉階層和下一代人利益的自由主義,這種左右對立的政治化很可能將反過來阻礙氣候治理的實質性進展。
全球氣候治理的新局面:“脫實向虛”
(一)為什麼“脫實”:現實倒逼下的逃避
首先,俄烏戰爭引發能源危機的影響。
俄烏戰爭導致俄羅斯輸送到歐洲的天然氣管道損壞,促使歐洲多國短期內擴大國內化石燃料儲備。這意味著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而且,受俄烏戰爭影響,歐盟天然氣碳排放量下降了10%。然而,歐盟以煤炭替換天然氣後消耗了更多能源,導致煤炭的碳排放量增加了6.7%[6]。各個國家脫碳減排的力度無法抵消不斷上升的全球總排放量,這一點在經過淡化的峰會決議文本中得到了反映。文本中加入了促進“低排放和可再生能源”的條款,儘管峰會追求的是“零排放”,但用的卻是“低排放”的字眼,體現了峰會對歐洲能源危機的妥協,更準確地說是對天然氣的認可,儘管天然氣比石油和煤炭更清潔,但仍然是化石燃料。世界各國領導人忙於處理不斷攀升的能源價格和高昂的生活成本,更不願意在淘汰化石燃料問題上採取大膽行動。
其次,全球通貨膨脹和經濟危機的影響。
2023年1月,世界銀行最新的綜合研究報告《全球經濟衰退迫在眉睫》顯示,隨著各國央行紛紛加息應對通脹,2023年世界可能走向全球性經濟衰退。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去年10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顯示,全球通脹將從2021年的4.7%上升到2022年的8.8%,但2023年和2024年將分別降至6.5%和4.1%[7]。同時,全球經濟活動普遍放緩且比預期更為嚴重,通脹處於幾十年來的最高水平。各國面臨著生活成本危機,多數地區的金融環境不斷收緊,再加上俄烏戰爭和新冠毒株持續變異擴撒——這些都抬升了經濟前景的風險。
(二)為什麼“向虛”:氣候問題的“政治化”和“道德化”
第一,氣候問題的“政治化”,西方“綠黨”影響政策走向。
歐盟在氣候問題政治議程的設定和發展中扮演關鍵角色,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在歐盟內部,歐洲的綠黨主張提高歐洲機制的民主性和透明性,包括強化歐洲議會的權力、監督歐盟委員會的法令起草過程等;在全球尺度,在歷次國際氣候談判中,歐盟都倡導以一種“規範性力量”建立氣候變化機制。
德國的綠黨是西方政治中不可小覷的一股左翼力量,直接影響著德國的內政和對外政策制定。在氣候變化與環境保護方面,德國綠黨希望與中國開展建設性對話,同時強調應對氣候變化不能以犧牲第三國或“人權和公民權利”為代價。在德國與中國開展的建設性合作中,德國聯合政府十分關心與中國共同在生態保護、氣候變化、碳中和等全球性議題的合作,這也是綠黨領導人強調“不能與中國切斷聯繫”的根本原因。應對氣候變化和生態保護等議題將是德國政府開啟中德進一步合作的突破口。

德國綠黨聯席領袖之一Annalena Baerbock
(圖源:路透社)
美國在氣候議題上的“政治化”也非常突出,兩黨對於氣候問題的態度幾乎截然相反。共和黨的特朗普曾經帶領美國退出《巴黎協定》,而後民主黨的拜登則在上任後讓美國重回該協定,兩年後美國大選可能的易主或許又會使美國再次退出。在美國,氣候議題的“政治化”不僅僅體現在國內,也體現在其外交政策上,這在《削減通脹法案》(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中充分體現了出來[8]。
2022年8月生效的總計約7400億美元的《削減通脹法案》分兩部分,“開源節流”和“調水”,目的是要減輕通貨膨脹水平和緩解氣候變暖。有關氣候政策的內容體現在“調水”這部分,即將4330億美元資金分配至以氣候變化措施為主的各領域,最終7400億美元收入中富餘的約3000億美元即為減少的政府赤字。為了在2030年實現相比2005年減少40%碳排放的目標,3690億美元被調度至用於改善“能源安全與氣候變化”。也就是說將大力發展新能源產業和更加註重能源安全。鑑於美國政壇政治利益和意識形態高於氣候變化議題,拜登政府急於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謀求全球領導權的戰略。該法案本身在美國兩院極化政治中施行將充滿不確定性和風險。
第二,氣候問題的“道德化”,公正問題凸顯。
在全球氣候問題“道德化”過程中,公正轉型與下一代的問題越來越引人關注。由於程序不公、權利義務不對稱等現象廣泛存在,阻礙了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COP26公正轉型宣言的出現,讓公正轉型一詞能見度提升。公正轉型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的勞工運動,當時美國和其他國家開始認真監管污染產業,同時認識到依賴這些產業維持生計的“人”和“社區”遭受的打擊。 2018年,“公正轉型”從地方的勞工運動發展成為全球範圍的運動,在波蘭煤炭城卡托維茲舉行的COP24上,世界各國政府通過了《西里西亞團結和公正轉型宣言》(Solidarity and Just Transition Silesia Declaration),指出“創造優質工作以及優質工作對於確保公眾支持長期減排和氣候韌性發展、並使各國能夠實現《巴黎協定》的長期目標來說非常關鍵[9]。”
表1:“公正轉型”發展時間表
|
年代 |
事件 |
|
1970 |
美國地方污染產業監管與勞工運動。 |
|
1990 |
美國工會與環保團體在地方污染問題與勞工間尋找解方。 |
|
2004 |
阿波羅聯盟,匯集200多個勞工、環境、商業和社會正義團體解決問題。 |
|
2018 |
“公正轉型”從地方勞工運動跨越到全球舞台,在波蘭煤炭城卡托維茲舉行的COP24上,世界各國政府通過了《西里西亞團結和公正轉型宣言》。 |
|
2021 |
COP26,16個北美和歐洲國家簽署公正轉型宣言。 |
|
2022 |
COP27,歐盟委員會和國際勞工組織(ILO)共同主辦了聯合國年度氣候大會上的首個“公正轉型”邊會(Just transition) |
製圖:IIA學術編輯組
中國應如何進行氣候外交:虛實並舉
第一,氣候外交的原則是去政治化。
在西方世界,甚至全球範圍內,氣候問題的政治化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正如過去和現在西方主導的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一樣,氣候問題也會成為一種價值觀被政治化。如今,西方正是在利用這些普世價值的政治化不斷地打壓中國、干涉中國內政,並在全球範圍內營造一種西方與中國的對立局面,即所謂的民主對“專制”、自由對“封閉”。在這樣的西方話語體系中,我們的話語是非常無力的,很難在西方主流輿論中被認真聆聽。

瑞典環保少女格蕾塔·桑伯格
含淚斥各國領袖不作為
(圖源:香港01)
面對不友好的外部環境,在對待氣候問題、開展氣候外交上,我們應該改變思路,避免把氣候問題政治化,外交的重點應該放在不做什麼和不說什麼上。
一方面,我們主觀上不能把氣候作為一種外交工具。例如,去年美國前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反制措施中最後一條就是“暫停中美氣候變化商談”。佩洛西竄訪台灣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政治和外交事件,是美國企圖以台製華、製造兩岸衝突的又一次嚴重挑釁,我們必須堅決予以反制。但是,採用什麼手段進行反制需要我們進一步思考,特別是涉及氣候問題這種典型的全球公共品。從這件事情來看,將“暫停中美氣候變化商談”作為反制措施似乎對美國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相反造成了西方世界的種種擔憂,即中國未來也會將台灣問題與其他全球公共議題掛鉤。將經濟貿易軍事等議題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是美國和西方常用的手段,但這些做法已經開始被國際社會和絕大部分國家所不齒,也已經在行動上表達出了各種不配合。
因此,對於中國而言,面對全球氣候治理這種具有明顯全球公共品特徵的議題,應該堅決避免政治化操作,更不應該將其工具化,作為外交手段來應用。我們應該要像堅持“不干預他國內政”那樣在外交實踐中堅持不把氣候問題視為外交工具。
另一方面,要讓別人相信我們沒有將氣候問題當作外交工具。可以說這是對於我們氣候外交最大的挑戰,因為西方主流媒體長期負面宣傳下的結果在短期內是很難改變的。因此,在氣候外交上,我們要調整宣傳的方式,特別是要區分對內和對外的話語。需要保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態,避免因黨政的過度宣傳給西方國家留下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空間。
第二,氣候外交的手段要“虛實並舉”。
在俄烏戰爭、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等多重危機下,全球氣候治理出現了“脫實向虛”的趨勢。這種變化會持續多久可能取決於全球應對其他危機的時間和效果,但是應對氣候變化和減少碳排放的大方向是不可逆的,這也意味著我們的氣候外交應該做到“虛實並舉”,不僅要講好中國氣候治理實踐的故事,而且要講好我們與西方世界共同的綠色低碳價值。
首先,要做好“實的”氣候外交,就要將中國故事數據化和案例化。
對於中國氣候治理實踐的各種案例,無論是成功的還是失敗的,都是我們氣候外交的關鍵素材,我們應該將這些素材數據化和案例化,並通過合適的組織在合適的場合呈現出來。我們認為關鍵在於把握住以下兩個問題:第一是講什麼,第二是誰來講。講什麼?我們要講述的氣候治理故事應該充分體現多元化,除了氣候治理主體的多元化,還應該充分體現氣候治理領域的多元化,這些多元化本質上就是我們中國故事的特徵和優勢。值得特別強調的一點是,也是我們過去相對避諱的問題,我們不僅僅要講述成功的案例,更要講述失敗的經驗,要在氣候外交中體現中國的立體性,以此改變西方世界對中國的刻板印象,也反過來提高中國故事的可信度和公信力。
誰來講?這是非常關鍵的問題,因為這將直接影響到中國故事本身的影響力。西方社會以及他們影響的全球各地在二戰以來逐漸形成了一種反權威的固化思維,對自上而下的信息有一種天然的抗拒。這與我們的文化和政治社會傳統截然相反。但是,簡單地以文化和社會差異來強調我們與西方的不同無法增進雙方的互相理解。因此,我們需要從西方的視角重新審視我們的外交策略,特別是目前全世界共同面臨的氣候變化這一新的課題。我們可以嘗試開闢一條自下而上的宣傳路徑,即通過NGOs、企業、學界和地方政府來講述中國的氣候治理故事。以NGOs為例,經過我們的調研發現,很多本土和境外的NGOs已經在中國開展了很多環境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這些都可以成為他們對外講述的故事,這些故事也更容易被世界各地方理解和接收。
其次,對於“虛的”氣候外交,可以用道家和儒家倫理對接西方“道德化”。
氣候問題本身是一個科學問題,由此產生的應對氣候變化這一議題則更多是一個經濟問題、技術問題和社會問題。如今,隨著對應對氣候變化議題討論的逐步深入,“公正”和“下一代”逐漸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或者說已經成為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實踐的基本前提,氣候問題已經慢慢成為一個道德問題,甚至是宗教問題。這是非常值得我們關注的趨勢。一直以來,一旦涉及到價值觀,似乎我們就與西方存在著不可彌合的鴻溝。但是在應對氣候變化,推進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上,我們的儒家文化事實上與西方如今倡導的公正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具有相同的內核。
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本質上是探討人與自然/地球的平衡發展問題,這本身就是道家和儒家討論的基本性問題,即天人關係問題。道家和儒家歷來主張“天人合一”,不將人和自然看作二元對立的主體,強調人可以通過認識世界的客觀規律來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道家主張自然和人類合而為一,人類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人類沒有權利破壞自然。儒家尊重和敬畏大自然的規律,同時也肯定人認識世界、而非改造世界的主觀能動性。儒家的“中庸之道”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表現為一種節制思想和觀念,即基於“取之有度,用之有節”的一種看似樸素實則科學的生態倫理觀。儒家要求人類以愛護和珍惜自然資源和環境為前提,有節制地開發和使用,以維持世間萬物的生生不息和人類的可持續利用。儒家提倡的天人合一和節制道德與如今西方社會盛行的“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是一脈相承的。
以道家和儒家倫理作為核心價值觀對接當前氣候問題的“道德化”從理論上是可行的。但是,在實際的氣候外交中,需要注意的是,我們應該盡可能避免強調道家和儒家倫理的中國特色,而應該突出道家和儒家倫理中各種觀點的普世價值,特別是大儒家文化圈對儒家倫理的共同認知和理解。共同提倡基於儒家倫理的綠色低碳價值,並與西方核心價值對接,以氣候問題為抓手,真正意義上擺脫西方對中國的價值封鎖和孤立。
註釋:
[1]Roadmap to US$100 Billion.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climate-finance-roadmap-to-us100-billion.pdf
[2]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https://www.ipcc.ch/sr15/
[3]台灣環境資訊協會,“氣候大會的終極困境:戒不掉的化石能源與緩慢的能源轉型”,2022年12月6日發佈於雅虎新聞。
[4]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戴兵大使在安理會‘非洲氣候與安全’辯論會上的發言,發佈於2022年10月12日,http://un.china-mission.gov.cn/hyyfy/202210/t20221013_10782602.htm
[5]Maslin Mark, Parikh Priti, Taylor Richard, Chin-Yee Simon , “COP27 will be remembered as a failure – here’s what went wrong”. Published on November 21, 2022. The Conversation.
https://theconversation.com/cop27-will-be-remembered-as-a-failure-heres-what-went-wrong-194982
[6]European Parliament's Committee on the Environment, Public Health and Food Safety (ENVI),
“The COP27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Status of climate negotiations and issues at stake”.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STUD/2022/733989/IPOL_STU(2022)733989_EN.pdf
[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應對生活成本危機”,2022年10月。
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2/10/11/world-economic-outlook-october-2022
[8]美國國稅局(IRS). https://www.irs.gov/inflation-reduction-act-of-2022
[9]Makower Joel (2021). "Just transition' is the new ‘net zero." Greenbiz.
https://www.greenbiz.com/article/just-transition-new-net-zero
本文作者
黃紫藍: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助理。
黃平: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國際事務研究院副研究員,科技創新與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高級公共管理研修項目中心學術主任。
*原創聲明:本文版權歸微信訂閱號“大灣區評論”所有,未經允許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轉載、複製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本文部分或全部內容,侵權必究。
GBA Review 新傳媒
評論文章
 如何“破局”与“共融”?——百川论坛“变革中的‘全球南方’:地缘政治与发展合作”2025研讨会在深启幕
如何“破局”与“共融”?——百川论坛“变革中的‘全球南方’:地缘政治与发展合作”2025研讨会在深启幕 練卓文:加強中歐合作應對當前的國際貿易挑戰
練卓文:加強中歐合作應對當前的國際貿易挑戰 包宏:美元——特朗普發動全球關稅戰的根源、底氣與死穴|經濟觀察
包宏:美元——特朗普發動全球關稅戰的根源、底氣與死穴|經濟觀察 王希聖:從「重新武裝歐洲計畫」到《歐洲防務白皮書》 ,歐洲安全能否離開美國?|戰略與安全
王希聖:從「重新武裝歐洲計畫」到《歐洲防務白皮書》 ,歐洲安全能否離開美國?|戰略與安全 俠客島對話鄭永年:我們要「超越關稅看關稅」
俠客島對話鄭永年:我們要「超越關稅看關稅」 俠客島對話鄭永年:特朗普關稅「休克療法」能醫治「美國病」嗎
俠客島對話鄭永年:特朗普關稅「休克療法」能醫治「美國病」嗎 鄭永年、段嘯林、袁冉東:深圳下一步發展的「三個共識」|全球灣區觀察
鄭永年、段嘯林、袁冉東:深圳下一步發展的「三個共識」|全球灣區觀察 中國和美國拼的是「經濟韌性」|獨思錄 x 鄭永年
中國和美國拼的是「經濟韌性」|獨思錄 x 鄭永年 「中美俄大三角」關係的現狀及其未來|獨思錄 x 鄭永年
「中美俄大三角」關係的現狀及其未來|獨思錄 x 鄭永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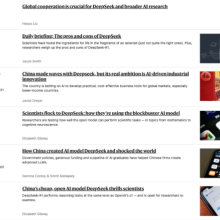 遊傳滿:如何「鉗制」DeepSeek?OpenAI如是說|全球法治觀察
遊傳滿:如何「鉗制」DeepSeek?OpenAI如是說|全球法治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