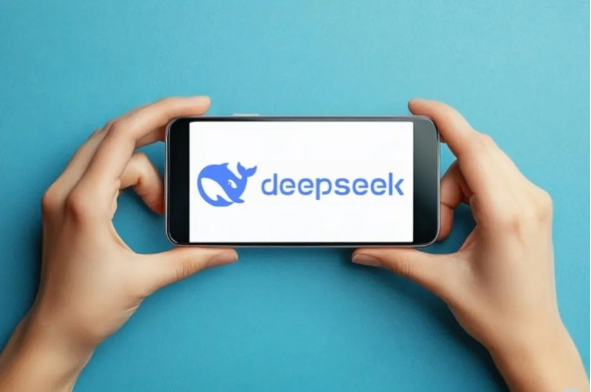Facts | Insight | Impact
独思录
Thinking
Alone
Prof. Zheng Yongnian
郑永年
08.16. 2024
第25录 编者按
美国两党之争局势升温。
在宾夕法尼亚州竞选集会上躲过暗杀短短五天后,特朗普登上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舞台上,正式接受提名并发表演说。特朗普抨击现届政府使美国衰落,面对通货膨胀危机、移民危机和国际安全危机,他承诺将在上任后解决这些问题,扬言要“使美国再次伟大”。与此同时,在民主党方面,7月21日拜登宣布退出竞选并支持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参选总统,这一决定改变了竞选的政策动向。8月6日,哈里斯选定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Tim Walz)为其竞选搭档。
郑永年教授指出,美国大选中两党之争并非一场简单的权力争夺战,而是一场更为深刻和深远的“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政治战争。二战后,民主党和共和党在经济、价值取向方面出现分裂:民主党向资本利益倾斜,提倡所谓更为“进步”的价值观,包括经济自由、族群、多元性别等;而特朗普版本的共和党把民主党视为是美国积弱的根源,需要通过激进的“重塑”在各个领域进行变革。郑永年教授强调,美国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在试图通过外部推卸责任而不是内部革命解决问题,但这并不能真正减轻美国国内的压力,面临严峻挑战,尽管两党候选人会不时地诉诸于“革命”,真正的革命依然可能是“不可能的使命”。
在国际政治层面,尽管国际冲突不断,但各国最为关切的无疑是美国大选。美国仍旧是当今世界的头号大国,内部的政治变局不仅会影响美国本身的发展,更具有巨大的外部性。如果人们对今天美国内部政治所经历的巨大变化的本质没有足够清晰的认识,那么大概率会犯外交层面的大错误,而对于被美国或者美国的盟友视为“敌人”的国家来说,更可能犯内政层面的颠覆性错误。
01 美国总统大选局势
依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7月15日,在特朗普正式获得共和党提名时,特朗普也宣布由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J·D·Vance)担任其竞选副手。7月18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落幕,特朗普领的“MAGA”派(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在共和党内部的势力迅速巩固。在民主党方面,7月21日拜登宣布退出竞选并支持现任副总统哈里斯(Kamala Harris)参选总统,这一决定改变了竞选的政策动向。8月6日,哈里斯选定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Tim Walz)为其竞选搭档。随着双方阵营正副总统候选人的确定,美国总统大选局势迅速升温。尽管谁输谁赢依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这注定又是一次非一般的异常惨烈的选举。
对这场选举的不确定性,美国的政治人物是最直接的感觉者。前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8月7日在接受美国MSNBC采访时说:“共和党已经被劫持了,它现在是一个邪教,他们(共和党人)应该把它夺回来,因为(美国)这个共和国需要一个强大的共和党”。实际上,这也是佩洛西迫使拜登退选的主要原因,因为在她看来这场选举已经关乎到美国民主的存亡问题。而现任总统拜登更为悲观。他在8月7日表示,如果哈里斯胜选,特朗普败选,那么他“不太有信心到时能和平移交权力(给哈里斯)”。特朗普至今坚持2020年败选是因为民主党窃取了他的胜利,拜登警示这次的结果可能也相同,因为“(对川普来说)他唯一会输的可能,就是胜选结果被偷走”。拜登的这种担忧并非毫无道理。特朗普在今年稍早就警告,如果他输掉2024年的总统大选,对美国汽车产业和全国都将是一场大屠杀。当时拜登与他的竞选团队很快就作出回应,称特朗普就是在扇动政治暴力。
当然,这是民主党政治人物对共和党的看法。在另一端,已经特朗普化的共和党对民主党的看法甚至更为恶劣。在特朗普的共和党那里,人们普遍的认知是,民主党已经是美国“积弱”的主要根源,因此,无论如何必须从民主党手中夺回政权,“让美国再次伟大!”
2024年5月6日,前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采访中猛烈抨击了前总统特朗普,称他为“暴徒”,并指责他将共和党变成了“邪教”(图源:Getty Image)
02 民主、共和两党之争
——“革命”与“反革命”之争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次总统选举并非一场简单的权力争夺战。这是一场更为深刻和深远的“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政治战争。
尽管这里的“革命”与“反革命”对研究者来说不是价值判断,而是对美国政党政治在左右派意识形态层面的分布的分析,但无论是对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来说,这无疑是一种价值取向。在西方的政治历史中,现代性的概念始于文艺复兴,确立于启蒙运动。在很多人看来,今天西方所取得的成就是“启蒙运动”这一“项目”的产物。之所以称之为“项目”是因为启蒙运动所确立的“进步”价值观念并非必然会发生,更并非必然会成功。之所以“并非必然”是因为“进步”的力量往往伴随着“反进步”的力量,即保守主义力量。正如牛顿力学所显示的,有“进步”,便会有“反进步”,有“革命”,便会有“反革命”。因此,近代以来,“左派”往往意味着“进步”,意味着“革命”,而“右派”往往意味着“保守”,意味着“反革命”。
在今天美国的政治系谱中,民主党被视为是左派,是“进步”的,而共和党则被视为是右派,是“保守”的。民主和共和两党之争也就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
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天美国两党之争的核心并不在一些具体的社会经济和外交政策,而是两党的价值之争。尽管两党也强调一些具体的政策,但强调这些具体的政策的目的是论证各自的价值观。
《纽约时报》(2024年8月7日)发文指出,民主党的策略更多是基于族裔、性别、文化归属的身份政治,而不是任何政策考量。这点很重要,民主党的确是根据这些来组织这次选举的。但需要补充指出的是,尽管这些表现为“策略”,但这一“策略”所承载的或者表现的便是民主党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共和党何尝不是这样呢?共和党更是一种身份政治,只不过表述方式不同罢了。
两党之间这种意识形态或者价值的分野并非新鲜。如果说美国独立革命所诞生的政治一直表现为进步政治,美国保守主义也从未消失过。远的不说,二战以来,民主党总是把自己和进步的观念绑在一起,例如(少数族群的)民权、工人阶级、妇女、环保、反贫困等。而共和党总是和保守观念绑在一起,例如资本、家庭、宗教、传统文化和价值等。
2023年1月22日,支持堕胎的示威者聚集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的州议会大厦,纪念罗伊诉韦德案50周年,当时拜登政府试图将堕胎权作为24年总统大选的战斗口号(图源:路透社)
03 被“第三条道路”改变的民主党
今天的美国政治局面可以直接追溯到里根革命。里根革命自称为“保守主义革命”。尽管里根革命似乎聚焦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这场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则是全方位的,并且其影响力深入到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其中,最主要的政治变化便是民主和共和两党路线在一些领域的“移位”。
这种“移位”的发生可以视为是民主党抢占了共和党保守革命的“果实”。里根保守主义革命(在英国是撒切尔革命)催生了美国(甚至整个西方)的内外部变革。在内部,新自由主义终结了自二战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所最终导致的经济滞涨状态,通过赋予资本前所未有的自由来促进快速的经济增长;在外部,新自由主义造成了新一波全球化,并且是“超级全球化”,即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面对这种情况,在克林顿时期(在英国是工党的布莱尔),民主党为了生存和发展,开始了路线调整,那就是当时盛行的所谓的“第三条道路”(既不主张纯粹的自由市场,也不主张纯粹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两者之间取折衷方案)。
“第三条道路”改变了民主党。传统上,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但“第三条道路”则让民主党不仅容纳了资本的利益,更是明显地向资本的利益倾斜。民主党因此接过了传统上共和党所秉持的一些价值观,包括经济自由、自由贸易、全球化等。在外交领域,传统上,共和党更倾向于使用暴力和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而民主党则倾向于提倡和平,反战。但自克林顿以来,民主党也倾向于甚至更倾向于使用暴力和战争。在前南斯拉夫问题上,民主党接受了“人权高于主权”的概念来论证其使用暴力的合理性。不难发现,至少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海外战争都是民主党相关联的。
今天,美国的民主党成为一种“怪异”的综合体。在包括经济和战争等越来越多的领域,民主党似乎更像传统的共和党,但同时,在族群、性别、文化归属等社会领域依然秉持其“进步”的价值观。实际上,在社会文化领域,民主党似乎变得越来越激进。例如,近年来围绕着“黑命贵”运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发生了“文化虚无主义”,甚至是“文化取消主义”,即用今天的观念去全面否定以往所发生过的实践。再如,在性别问题上,民主党是LGBTQ(彩虹族)的承认者、接受者和积极推动者。又如,在移民问题上,民主党一贯持放任自由的态度,大量非法移民的涌入不仅影响美国经济,更影响美国的选举政治。这使得支持共和党的埃隆·马斯克较早前发文说,这可能是美国人(公民)最后一次投票了。
在一些国家(包括中国),民主党的这些立场性变化被视为是“白左”。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推动这些观念和基于这些观念之上的社会运动的不仅是“白人”群体,更是少数族群。经验地看,所谓的“白左”是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的。有人说,这是因为民主党的选票考量。选票的考量的确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都是民主党传统上所秉持的价值和原则。如果从启蒙运动的视角来看,这些观念无疑具有“进步性”。
2024年7月22日,“黑命贵”运动在一份声明中呼吁民主党领导人允许公众参与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而不是将其交给党代表决定,而就在几个小时前,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刚刚获得足够的代表锁定提名(图源:路透社)
04 共和党的“反革命运动”
如果说民主党代表的是“革命”,那么特朗普化的共和党所代表的则是“反革命”。特朗普第一任期自称为“保守主义革命”。经过了这些年的变化,现在把这场保守主义革命称之为是“反革命运动”更为合适。
首先,这场运动是反应性的,是对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反应。里根革命之后崛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尽管使得美国更加富裕了,但今天美国社会的分化也是史无前例的。社会充满着各种矛盾,包括种族之间、阶级之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等。所有这些矛盾最终汇聚到政治和政党,表现为两党之间的党争。就内政来说,美国两党今天几乎很难找到任何共识了。
第二,这场运动是对民主党路线的反动。特朗普并不认为所有这些都与共和党自身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有关,而是相信这是和民主党版本的“自由主义”政策有关,并把民主党视为是美国积弱的根源。因此,特朗普化的共和党不仅想夺回权力,更想夺回路线阵地。特朗普从第一任选举开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拉票活动,从来没有忘记提醒其支持者,只有赶走了民主党,他领导的共和党才可以“让美国再次伟大”。
第三,特朗普“反革命”的目标是重塑美国经济社会,并且这种重塑需要通过激进的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各个领域变革。
尽管民主与共和两党已经各自发表了自己的选举政纲,但是没有多少人真的去关注选民应当去关注的一些问题:两党所宣布的政策是否合理?两党是否有能力去兑现其承诺?不同的政策会导致怎样的后果?美国民主理论假设,选民应当对这些问题加以理性考量,因为选民选举的不是总统个人,而是他(她)所代表的政策。
但是,“选民应当对这些问题进行理性的考量”可能只是一个理论假设,在实践中或许很少发生,因为没有几个选民有能力获取分析这些问题的充分的信息及其得出基于分析之上的理论和结论。近几十年来,尤其是出现社交媒体以来,美国的选举越来越被候选人个人的因素所影响。自从特朗普出现以来,选民实际上已经不需要考虑这些问题,因为特朗普成功地把政治和政策转化成为选民对其个体的认同。“个体”不仅仅指候选人的个人魅力,更重要的是指候选人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标识等因素。如果说候选人所代表的政策还能“量化”,所有这些软性的特质是很难用任何数字来衡量的。今天,正是这些软性的东西主导着美国的总统选举。
2023年3月17日,谷歌解除了在 2021年1月6日国会山发生骚乱后对特朗普实施的长达两年多的YouTube禁用令(图源:路透社)
而这也正是美国社会高度分化、两党高度对立的反映。这从美国选举越来越高的投票率中可以看出。在4年以前(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投票率创120年来新高,有超过1.59亿美国人在这次总统大选中投下了选票,投票率为近70%。相比之下,2016年民主党希拉里和共和党特朗普的对决中,投票率为56%,2008年民主党奥巴马和共和党麦凯恩的对决中,投票率为58%。在民主国家中,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比利时都有强制投票的规定,因此投票率很高,在80%上下;美国没有强制投票的规定,投票率大约在55%,在35个民主国家中排名30位左右。
美国学者对美国的投票率低有各种解释,例如美国人根本没有投票意愿,认为选举系统受人操纵,他们的票数没有影响力,美国政府也不代表人民的意志。又如,不投票,是因为人们一般不太关注新闻,没有足够的信息来投票。但实际上,投票率低和一个社会的高社会信任度有关。投票是有成本的,除非不得已,人们不会选择去投票。以往,美国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中产阶层拥有共识和信任,投票率就低。现在,美国社会中产群体萎缩,社会分化,社会没有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只相信自己手中的选票,认为只有自己手中的选票才能改变现状。这种情况自然导致投票率的高涨。
中产阶层萎缩更直接指向了中间选民萎缩甚至趋于消失的事实。从前,美国的中间选民(即立场模糊者)庞大,两党如果要赢得选举,那么必须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但现在这个群体的规模已经大大萎缩,选民立场鲜明,要不支持民主党,要不支持共和党。在这样的情况下,选举倾向于成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争。
美国2016年大选投票率与其他发达国家和最近几次大选投票率对比图(图源:statista)
05 美国面临高度分化危机
无论是特朗普挑选万斯作为搭档,还是哈里斯挑选沃尔兹作为搭档,都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考量的结果,而非传统上选票考量的结果。
当特朗普选择万斯作为其竞选搭档时,敏感的人们就意识到,这个选择与其说是为了选票,倒不如说是为了极端的右翼意识形态。人们发现,在过去八年里,万斯的人生经历了快速的变化,从一个畅销书作家和高调的特朗普批评者,变成了特朗普最坚定的捍卫者,现在又成了他未来的副手。在竞选公职之前,万斯曾以畅销回忆录《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闻名,这本书讲述了他在一个贫穷家庭的成长经历,同时也是从社会学角度对美国白人工薪阶层的审视。这本书出版于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的那个夏天,在特朗普获胜后,许多读者把这本书当作一种指南,来了解特朗普获得白人工薪阶层社区支持的原因。万斯本人在2016年竞选期间曾严厉批评特朗普。但到2022年,他接受了特朗普,在后者的支持下赢得了一场竞争者众多的共和党参议院初选,并成为国会中支持特朗普的可靠声音。也就是说,特朗普选择甚至比自己更具“特朗普特色”的搭档。
在另一端,民主党也紧随其后。当哈里斯宣布沃尔兹作为搭档时,美国媒体说,这是哈里斯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国会山庄报》(The Hill)(2024年8月6日)发文指出,这并不是说沃尔兹是世上最糟的选择,但宾州是关键的摇摆州之一,可能是哈里斯打这场选战中最重要的州,而夏皮洛(Josh Shapiro)是州长——他在当地的支持率高达 64%,单是这事实就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反之,沃尔兹是明尼苏达州州长,而哈里斯应该能轻松在明尼苏达州获胜。更为重要的是,选择沃尔兹并没有平衡哈里斯是个“旧金山自由派”的说法,反而强化了这种左翼形象。但正如另一媒体《纽约时报》所指出的是,沃尔兹在自由主义议程上与哈里斯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支持保护堕胎权、限制枪支,以及扩大带薪家务假等福利。在很多方面,沃尔兹被认为比哈里斯本人更左。而这也是民主党所要取得的效果。因此,当特朗普团队给沃尔兹起攻击性和讽刺性极强的外号“卫生棉条蒂姆”(在任明尼苏达州州长时,沃尔兹签署了一个法令,要求从四年级到十二年级的男厕所里也要提供卫生棉条),民主党反而开心笑纳和跟着喊的原因。
2024年8月6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副总统哈里斯和她的竞选搭档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抵达费城参加竞选集会(图源:美联社)
很显然,这是一场极端右翼和极端左翼之间的较量。尽管民主共和之间的“革命”与“反革命”谁胜谁负直到选举结果出来之后才能明了,但无论就“革命”还是“反革命”来说,大概率都会是以失败告终。
在今天的美国,无论是“革命”还是“反革命”,都面临巨大的制约因素。首先,所有政治行动都必须在现有的政治构架内进行。特朗普的支持者在特朗普第二次选举失败时,曾经以占领国会山的方式尝试挑战现成体系,但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果特朗普败选,一些人(包括现任总统拜登)对政权的和平移交存在疑虑,但人们可以确认,不管发生什么,特朗普不至于推翻美国现存制度。第二,美国已经确立了诸多领域的“政治上正确”,并且“政治上正确”影响选票,因此即使特朗普当选,其在内政方面的极端性也是有限度的。第三,两党判断的“失误”。对今天美国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把此归结为外在要素,即所谓的来自中国的“竞争”或者“威胁”。但把责任推到中国并不能解决美国的内部问题,把重点放在外交层面并不能真正减轻国内的压力。第四,美国社会分化到今天这一地步,没有一个政党有能力去重新组织社会。以往,民主是美国社会的核心组织方式,但今天民主反而成为继续分化社会和恶化分化的有效机制。
简单地说,今天的美国是一个需要革命、但没有革命机会的社会。面临严峻挑战,尽管两党候选人会不时地诉诸于“革命”,但真正的革命可能是“不可能的使命”。
如果内部“革命”(或者“反革命”)不可行,那么人们就要担心外部的战争了。近代以来,至少西方的历史表明,内部革命或者外部战争是解决内部矛盾的两种最有效的方法。如果今天的美国两党对内部矛盾束手无策而继续外化内部矛盾,那么战争的发生甚至比内部革命更有可能。如果那样,人们就有可能面临另一场世界大战。这也就是人们必须关切美国选举的原因。
| 原创声明 |
本文版权归微信订阅号“大湾区评论”所有,未经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复制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本文部分或全部内容,侵权必究。公众号授权事宜请直接于文章下方留言,其他授权事宜请联系IIA-paper@cuhk.edu.cn。
GBA 新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