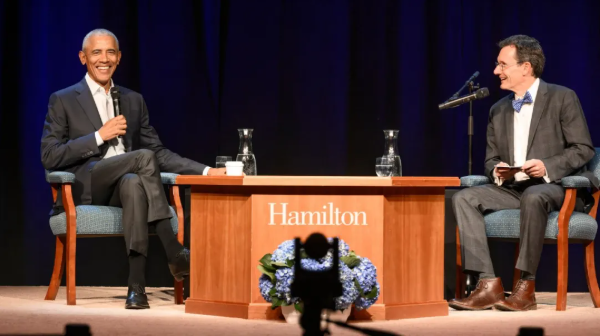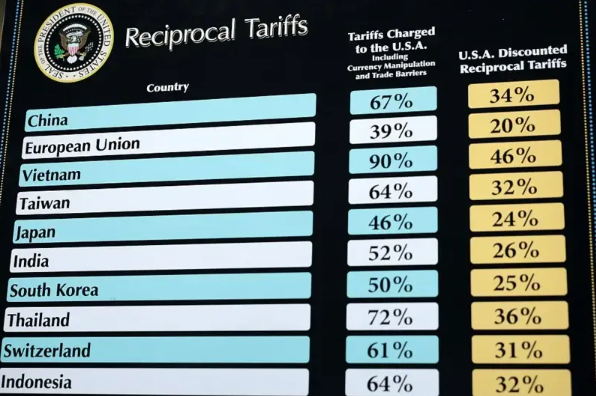Facts | Insight | Impact
獨思錄
Thinking
Alone
Prof. Zheng Yongnian
鄭永年
編者按
近年來,美國政府不斷加碼在人工智能領域的佈局。在外交領域,2023年11月9日,美國國務院發佈其首項人工智能戰略,計畫在美國國務院推動人工智慧創新、基礎設施、政策、治理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設與應用,進而增強美國的外交能力。該戰略提出了的基本目標包括構建安全的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制定人工智能治理政策和指南、人工智能數據的訪問和使用等。
最近,人們對「DeepSeek是否應該開源」的討論,更表明了人類對人工智能可能使用不當的擔憂。無論人工智能是「賦能」還是「去能」外交,可以肯定的是,這一決定人類發展方向的技術必然會成為未來中美外交的主軸。如何面對人工智能對外交帶來的影響,將成為世界各國必須面對的課題。
全球範圍內,人類已經面臨一個人工智能時代,而對很多國家來說,世界已經進入了人工智能時代了。人們已經開始關切人工智能對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和角角落落的影響,其中包括外交。的確,人工智能的「賦能作用」或者「去能作用」已經變得日益顯著,在外交領域也一樣。但是,正如我們下文要討論的,人工智能和外交的關係並非僅僅是前者對後者的影響。人工智能和外交既表現為人工智能對外交的影響(即implications),也表現為人工智能在外交領域的應用(即applications)。外交的永恆主題關乎戰爭與和平,因此,探討人工智能與外交的關係是有意義的。
要討論兩者之間的關係,就首先需要理解「前人工智能時代」(即沒有人工智能的時代)的外交。
01 「前人工智能時代」的外交
通常來說,外交是指一個國家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活動,通過類似互派使節、進行談判、會談等手段,意在建立能夠滿足彼此需求的關係。儘管其他組織例如政黨、城市、地方政府、大型企業(尤其是跨國公司)也扮演外交角色,但近代以來的外交主體是各國政府。
(一)外交的核心精神
人們常說「弱國無外交」或者「小國無外交」——這是對歷史和現狀的真實高度概括。中國近代所受的恥辱是「弱國無外交」的象徵,而今天烏克蘭正在經歷的便是「小國無外交」的象徵。不過,儘管外交背後是國家之間的實力較量,外交依然有其光輝的一面。外交的核心精神在於人類通過施展自身的理性精神以最小的成本獲得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正如「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概念所示,外交就是要追求國家利益的。人們對「國家利益到底是誰的利益」一直存在爭議,很多人並不認為存在抽象的國家利益,例如傳統社會就是君主的利益,現代社會可能是一個社會的統治集團的利益、某些政黨或者某些階級的利益。儘管如此,人們也很難否認國家利益的存在,例如近代以來的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和其他方方面面的國家安全的確存在著,並且這些利益是超越所有政黨、階級和社會群體的。
當地時間20日,烏克蘭外交部長瑟比加在社交媒體上表示,他會見了到訪的美國政府烏克蘭和俄羅斯問題特使基思·凱洛格(圖源:央視新聞)
儘管外交發生在方方面面,包括經貿、科技和文化交流等等,但外交的核心在於關乎戰爭與和平的全過程。其他方面的外交更類似於人們經常所說的外事活動,而外事活動的主體不僅僅是政府,也包括非政府組織,尤其是今天的跨國公司和國際性社會組織。外交貫穿於從維持和平到結束戰爭的全過程。很多人認為,外交最顯著的特徵可以說是預防性外交,這不難理解。預防性外交是一些為了避免國際之間爭端、避免爭端演變衝突,或是避免衝突擴大而進行的外交措施。因為國家利益的不同,國家之間總會發生衝突和摩擦,這就需要外交來解決。如果解決不了,國家之間就會發生衝突甚至戰爭,而衝突和戰爭亦需要通過外交來解決。衝突和戰爭解決之後,更需要外交來維持和平。
考慮到世界上強國和弱國、大國和小國並存的局面,外交的作用變得更為顯著。各國相處正如各個社會群體的相處,大國和強國經常欺負小國和弱國。很顯然,弱國和小國很難獨自抵禦強國和大國,因此對弱國和小國來說,外交經常表現為多邊外交,通過多邊外交在幾個弱國和小國之間形成聯盟來抵禦強國和大國。
(二)外交的手段
外交是典型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即目的證明手段的正確。這一點如果應用在個人層面或者用於處理一個國家的內部問題,那就很容易遭人譴責,往往被視為是不道德的。但如果用在處理國家之間的關係,則很少遭到有人譴責。因此,歷史和經驗地看,外交的手段是多樣的。
1、金錢外交
即有關國家使用金錢或是其他貨幣政策來達到其外交目的。這種形式被廣泛使用,無論是大國還是小國。金錢外交往往被視為是最理性的外交。
2、人質外交
即一個國家為實現外交目標而透過拘留或劫持人質的外交手段。這經常是弱小國家經常用來向強國施壓的一種不對稱外交。
3、炮艦外交
一個國家使用軍事力量來達到影響其他國家的目的。這是近代以來西方列強經常使用的外交方式,是帝國主義外交的主要外交形式,大部分非西方國家淪落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而很多國家被迫與列強簽訂了大量的不平等條約。
4、綏靖外交或者姑息外交
即通過在某些可能導致戰爭的事務上作出讓步,來避免戰爭的外交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歐洲對納粹德國的行為被視為是綏靖主義外交。今天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結束俄烏戰爭問題上所採用的方法也被歐洲視為帶有綏靖主義色彩。
5、核武外交
指有關避免核武器擴散及核戰爭的外交舉動,尤其是相互保證毀滅的外交政策,也就是對立的兩方大量部署核子武器,如果有一方全面使用核子武器,則會造成兩方都毀滅的恐怖平衡政策。
6、通過國家內部活動來影響國際社會
不過,外交不僅發生在國際舞臺上,更經常發生在一個國家的內部,即通過內部活動來影響國際社會。例如,「抗議外交」,即一個小國和弱國經常組織大規模遊行示威活動來抗議另一個大國或者強國,以便引起其他國家的關注。又如,當代日益流行的所謂的「公共外交」,更是一個國家借由傳播或溝通來影響另一個國家的民眾,而不是直接影響該國的政府。
以色列連日來持續爆發大規模遊行示威活動,大批民眾走上街頭抗議以軍恢復在加沙地帶的軍事行動(圖源:央視新聞)
02 「人工智能時代」的外交
那麼,人工智能和外交的關係到底是怎樣的?人們必須意識到,人工智能絕對不是一個產品,也不是一個行業,甚至不是一個領域。如果應用得當,人工智能是科研、教育、製造、物流、運輸、國防、外交、執法、政治、廣告、藝術、文化或者人們可以說得出來的所有事務的賦能者;但如果應用不當,人工智能也可以是所有這些事務的去能者甚至是取代者。
比較而言,人工智能和從前所有工業革命所產生的技術不同。之前產生的所有技術都是人類的工具,為人類所創造,也為人類所使用,用來提高效率。而人工智能不同,它已經是我們人類生活的內在部分,並且從體力到腦力,我們深受人工智能的影響。儘管人工智能是人類創造的,但人工智慧反過來在重塑我們人類。
儘管這些並非全都是外交,但人工智能和外交的關係正在變得越來越複雜。簡單地說,人工智能至於外交的意義在於我們把非人類的智能整合到人類活動的基本構架之中,成為人類活動內在的一部分。
我們這裏要討論的並非僅僅是人工智能對外交的影響。就人工智能和外交的關係來說,至少人們需要思考這三個層面的關係:
第一,人工智能賦能外交或者去能外交,也就是人們所說的人工智能對外交的影響,賦能為積極的,去能為負面的;
第二,人工智能作為談判對象的外交,即國家之間就人工智能對外交(或者國家安全)所產生的影響進行外交;
第三,人工智能的「自主外交」,即人工智能本身作為外交的主體而對一個國家的外交所產生的影響,儘管這方面現在還不那麼清楚,但這個時代正在很快到來。
對這幾個方面的關係,我們這裏可以作些初步的討論。
(一)人工智能「賦能」或「去能」外交
儘管人工智能是基於互聯網平臺之上的,但其意義已經大大超出了人們的想像。經驗地看,在不長的時間裏,一些大的網路平臺所集聚的用戶基數超過了大多數國家甚至一些大洲的人口規模。如果說,外交是為了影響對方國,無論是政府還是民眾,那麼互聯網平臺本身就在扮演一個外交角色。今天,無論是外交官個體還是各個外交組織(包括試圖影響外交的組織),都在高頻率地使用各種社交媒體作為外交的工具。不僅是外交官,各國政治人物都在使用社交媒體對內外事務施加影響,其中,最為典型的是美國總統通過運行自己的社交媒體來影響內外事務。
特朗普社交平臺帳號截圖:當地時間8日,特朗普在其自創社交平臺發佈一張「新地圖」(圖源:環球網)
1、人工智能「賦能」外交
在這方面,人工智能的賦能作用是顯然的。在收集資訊和處理資訊(這是傳統外交的核心)方面,人工智能可以幫助外交系統提高效率。經過訓練的人工智能,它的行動速度通常比人類的認知速度要快得多。如果作為一種賦能,人工智能無疑是積極正面的。
在賦能方面,人工智能也有潛力變弱國為強國,變小國為大國。人工智能可以在大國和小國之間、弱國和強國之間塑造一種不對稱對抗。一旦一個弱國或者小國掌握了足夠的人工智能,無論是其本身所擁有的還是來自外援,那麼就有能力抵禦和對抗一個強國或者大國。這種現象已經發生在俄烏戰爭中了,尤其是早期。烏克蘭之所以能夠抵禦來自俄羅斯的強大攻勢,與來自歐美國家的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援助」分不開。人工智能賦能表現在方方面面,無論是輿論戰還是軍事戰場上。
2、人工智能「去能」外交
在賦能的同時,人工智能也在對外交發生去能化的作用。賦能比較好理解。去能表明人工智能能夠有效阻礙甚至廢除現存外交家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給外交帶來嚴峻的挑戰,甚至是致命性的挑戰。去能至少表現在如下各個方面。
首先,人工智能在賦能外交系統的同時也在賦能其他很多社會角色直接參與外交活動或者踐行會對外交產生深刻影響的活動,而賦能其他角色往往意味著弱化外交系統的能力。
這個主題早已經由英國政治經濟學家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在其1996年出版的《國家的撤退》(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一書中提出,只不過那個時候人工智能還沒有開始發揮其像今天這樣的作用。斯特蘭奇認為,傳統上那種認為主權國家是國際事務上的主體的觀點已經不成立,跨國公司和國際非政府組織等非主權國家主體已經登上國際政治經濟舞臺。毫無疑問,今天人工智能在發揮的作用遠超跨國公司和國際非政府組織。
今天,集聚在網路平臺上的大量用戶不是受傳統地理意義制約的社會群體,他們更為分散,甚至沒有「身份」。儘管如此,網路平臺已經和國家或者政府構成了競爭。很多社會經濟的職能本來屬於國家或者政府,但如今網路平臺已經佔據了這些原本屬於國家的職能,並且在數量和規模上超過大多數國家和政府。經驗地看,一些網路平臺雖然以商業實體的形式運行,但就它們的規模、職能和影響而言,它們正在成為地緣政治和外交上的重要角色。
儘管網路平臺之間的競爭可能是商業性的,但各種競爭都已經影響到政府之間的地緣政治競爭,甚至越來越成為各國外交議程上的頭等大事。從政府的角度來看,網路平臺已經成為個人生活、國家政治話語、商業活動、公司組織甚至政府職能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或者說,網路平臺的商業行為越來越具有政治性質。
美國Meta公司刪除7700多個中國宣傳帳號(圖源: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其次,網路平臺運營商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也不見得一致。
很多時候,網路平臺傾向於用戶的利益,至少它們首先不會優先考量國家利益。這或許是因為網路平臺的利潤優先考量原則,又或許是因為它們對國家利益的認知和政府的不一致,也或許是因為它們沒有意識到它們的行為對國家利益的影響。
網路平臺對國家的影響是矛盾的。所有國家都希望自己擁有更多更大的平臺,因為這是國家力量的載體;同樣,平臺希望自己擁有更多的客戶,因為服務的人越多,它對用戶的價值就越大,越有吸引力。但同時,必須意識到平臺越多越大,國家和平臺也就越脆弱,因為越多越大意味著國家和平臺暴露給假消息、裸露、欺淩、仇恨、毒品和暴力等網路行為的攻擊的可能性就越大。今天,社交媒體在傳遞和操作政治資訊和虛假資訊方面的能力表明,一些網路平臺承載的職能已經影響到國家治理的實施,更不用說外交了。
再者,人工智能只有機器理性,而沒有像人類那樣的政治忠誠和政治判斷。
作為賦能的工具,人工智能的使用者是多樣的,不同的人使用人工智能以達到不同的目標。最近,人們對「DeepSeek是否應該開源」的討論就表明了人類對人工智能可能使用不當的擔憂。儘管開源有利於科學的發展,不開源最終會導致落後,但對「開源應該到什麼程度」人們並沒有共識。如果一種技術完全開源,例如核武器製造技術,那麼從理論上說更多的人就會知道如何製造核武器。如果這樣,這個世界就危險了。因此,AI教父辛頓最近就認為,DeepSeek開源了權重,類似在散播核裂變材料。這個比喻不見得恰當,但也指向了人工智能技術所能帶來的危險。
(二)人工智能作為談判對象的外交
預防一種新技術對國家安全所能帶來的威脅可以說是預防性外交的主題。這裏最合適的類比是核武外交。當美國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中第一次核武器試爆成功之後,美國「原子彈之父」物理學家奧本海默就引用印度佛教經典《薄伽梵歌》中的詩句說,「現在我成了死亡本身,世界的毀滅者」。自此開始,美蘇兩國拉開了核武外交,最終形成了所謂的“相互確保摧毀”(MAD)。在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之後,美蘇兩國進行了長期而艱苦的外交談判,在20世紀70年代簽署了《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和《反彈道導彈條約》,在1991年簽署了《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美國資深外交家基辛格先生是美蘇談判的經歷者。在他生前的最後一個階段,他的注意力放到了人工智能的崛起對國家安全和國際關係的影響,並把之置於中美關係之中。如果核武器是美蘇冷戰時期雙方可以確保互相毀滅的技術,那麼人工智能無疑是另一種可以確保互相毀滅的新技術。而這次輪到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了。很顯然,在蘇聯解體之後,美國已經把中國界定為唯一一個有能力和意願在全球範圍內對美國構成競爭和威脅的國家。在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看來,人工智能競爭已經構成了中美關係的主軸。
1973年1月23日,基辛格(左三)在巴黎簽署《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圖源:人民日報)
基辛格對這種競爭的後果看得很清楚,並且比誰都更早意識到了這一點。因此,促成中美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對話或者談判成為了「基辛格外交」最後的遺產。在他首次秘密訪問北京及此後中美兩國關係實現突破而建交半個世紀後,他最後一次飛往北京。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會見了他,會談的一個主題便是人類所面臨的來自人工智能的風險。這是他的最後一次出訪,也是他執行的最後一次外交使命。這次使命也促成了中美兩國元首把人工智能列為雙方會談的一個重要議題。
(三)人工智能的自主外交
即國家間的人工智能之間的外交。儘管對很多人來說,人工智能的自主外交還處於想像階段,但實際上這個進程已經開始了。一旦當人工智能有能力作出自主決策,它就超越了其工具性質,那麼就會出現意料不到的事情。人工智能根據自己的思維邏輯來運行,它不同於人類的思維過程,而且往往比人類的思維更快。研究者發現,人工智能會發展出自己的方法來實現其目標函數所指定的任何目標。它產生的結果和答案不具備典型的人類特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獨立於國家和企業文化。人工智能具有在全球網路平臺上對資訊進行監控、遮罩、裁剪、製作和分發的能力,而如今人工智能又將這些複雜性引入了不同社會的「外交空間」。
在這樣的情況下,無論對「進攻方」還是「防禦方」來說,包括虛假資訊的傳播和打擊虛假資訊的努力,都將變得越來越自動化,並由人工智能來執行。實際上,不斷進化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PT已經展示了創造合成人格的能力,人類可以利用它們產生具有仇恨言論特徵的語言,並用這些語言與人類用戶進行對話,以灌輸偏見,甚至慫恿他們使用暴力。
這樣的發展已經影響到了外交,尤其是人們所說的「公共外交」。儘管今天各國都想用人工智能來發展所謂的「軟力量」外交,尤其在民間外交或者公共外交層面。但是,人工智能的「軟力量」外交基本上走向了反面,因為由人工智能參與的「軟力量」外交不是互相交流和理解,更不是互相認知和認可,而是互相「妖魔化」,製造互相的仇恨。這是一個大趨勢。要意識到,現在的互聯網上的資訊依然以人類所生成的資訊為主體,而人工智能所產生的資訊為輔。但很快,互聯網的主體會被人工智能生成資訊佔據,互聯網也會因此變成一個巨大的「垃圾桶」,而這一「垃圾桶」無時無刻不影響著人類的生活和國家間的關係。
一旦人工智慧實現「自主」,那麼我們前面所提到過的各種外交形式,包括「炮艦外交」、「金錢外交」、「綏靖外交」、「人質外交」都可能在不同國家的人工智能之間發生,並導致意想不到和超越人類控制的結局。2017年,由穀歌旗下DeepMind公司開發的人工智能程式AlphaZero擊敗了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際象棋程式Stockfish。AlphaZero所採用的戰術極其獨創和詭異,它會棄掉那些被人類棋手視為極其重要的棋子,甚至包括像皇后這樣的強力棋子。它的走法並非源自人類的指導和指令,而且很多情況下,這些走法是人類根本未曾考慮過的。AlphaZero並沒有人類意義上的「戰略」;相反,它有自己的邏輯,能夠在紛繁複雜的眾多的可能性中識別出那些人類理性無法完全理解或者加以利用的走子模式。沒有人可以保證,這種人工智能生成自主戰略邏輯的情況不會發生在外交領域。
03 人工智能——中美外交的主軸
人工智能對中國外交所帶來的挑戰和衝擊會是難以想像的。人類進入互聯網時代之後,至少就公司的數量來說,互聯網企業高度集中在中美兩國。而進入人工智能時代以來,這種局面依然沒有改變。世界普遍認為,人工智能時代的競爭主體就是中美兩國。儘管中美之間存在著廣泛的外交領域,但較之人工智能,其他所有方面都顯得相形失色。人工智能依然處於快速發展的階段,而中美對人工智能的討論還處於早期階段。不過,可以相信,人工智能無論是發揮「賦能」作用還是「去能」作用,這一可以決定人類發展方向的技術必然會成為中美外交的主軸。
GBA 新傳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