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冷战结束后,国际制度成为大国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大国围绕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的竞争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走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导读 · 2023.07.06
冷战结束后,国际制度成为大国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大国围绕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的竞争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走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田野教授从“报酬递增”视角来解释当前大国何以重视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的竞争,分别阐述了报酬递增的思想源起、国际制度的报酬递增机制并给出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相应案例。他指出,在协调效应、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的作用下,在国际制度领域中的初始优势很可能转化为长期优势,促使大国在这一领域进入竞争状态。他认为,随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与新兴议题的出现,中国有可能通过国际规则的制定获得先发优势,实现“换道超车”。
本文由IIA学术编辑组根据田野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的百川论坛——“第二届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与高水平对外开放2023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而成。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核心问题是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传统上把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看作是合作的一种工具,但是国际规则和国际制度也可能成为大国竞争的工具。在此呼应本届论坛主旨说明中提到的“我们要深刻认识到规则的制定权已经成为中美竞争的核心,中国最有效的应对方法就是实施第三次开放,要注重话语权和规则问题,强化规则就是生产力的历史”。“规则是生产力”,这是经济学的一种表述。我们也可以说“规则就是权力”,这是政治学的一种表述。至于规则何以成为一种权力,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探讨当下的全球经济治理,很难脱离中美竞争的背景。中美的国际规则、制度之争不仅很大程度上塑造中美竞争的形态,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美竞争的结果。中美之间的竞争会不会转化成中美之间的冲突?在2022年11月巴厘岛的习拜会上,两国最高领导人都提出两国的竞争不能够转化成冲突。拜登说,美国要同中国激烈竞争,但是竞争不能够转化为冲突。总书记则指出,竞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存在,但竞争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竞争,不应该是你死我活的竞争。

2022年11月,巴厘岛中美元首会晤现场
(图源:央视网)
相对而言,地缘竞争很容易使竞争转化为冲突。如果中美竞争是以制度之争、规则之争为主,这种竞争很有可能是一种相对良性的、具有兼容性的竞争,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对这样一个制度之争、规则之争进行理论上的讨论。
报酬递增(increasing returns)的思想源起
在国际制度理论中,已有学者从报酬递增的视角,对制度变迁问题进行过讨论。比如,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在2001年出版的书《胜利之后:战后制度、战略约束与秩序重建》(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就采用了路径依赖和报酬递增的假设,来说明制度在报酬递增克服无政府状态、均势和战略敌对方面的潜在意义。在当时冷战结束不久的情景下,他的核心问题是霸权国在最初确立霸权的时候,如何运用国际制度达成其战略目标。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就是“霸权之后”这种国际制度是否还具有重要的意义,加之他的理论还有一些局限,需要我们进行更多的思考。
在冷战结束以后,伊肯伯里强调的是霸权国和弱国各自对国际制度都有需要,而今天我们看到更主要的问题是“守成国和崛起国应该如何看待国际制度”。伊肯伯里更多地是在制度和实力之间来考察霸权国的选择以及弱国的选择,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守成国和崛起国在实力接近的情况下如何在不同制度间竞争。另外,伊肯伯里虽然提到了报酬递增的假设,但是他主要是从制度变迁的成本,特别是沉没成本出发来考察,实际上报酬递增的含义远比“制度变迁成本”更为丰富。
报酬递增是指投入增加会导致产出更大比例的增加,是一种重要的正反馈机制。但正反馈还有其他的机制,比如说螺旋模式就不属于报酬递增。我们经常也把报酬递增和路径依赖放在一起使用,但实际上报酬递增只是导致路径依赖的重要原因之一,路径依赖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先后次序的不可更改,这也不属于报酬递增。所以我们需要对报酬递增本身进行探索。
报酬递增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在《国富论》中就提到了分工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分工也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它的潜在含义就是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也是经济进步的结果,因此出现了一种累积的因果演化。这个思想在在杨格(Allyn Young)1929年发表的《报酬递增与经济进步》中得到清晰的阐述,所以这个思想就被命名为斯密-杨格定理(Smith-Young Theorem)。这样一种报酬递增的现象,在多个领域中都有发现。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就是从报酬递增中理解制度变迁的问题,他指出,报酬递增及以交易成本为特征的不完全市场塑造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使其在总的方向上难以逆转。诺斯考量的是经济制度中的报酬递增,在政治制度中是不是还存在这种报酬递增,甚至这种报酬递增现象更为显著呢?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图源:the Economist)
国际制度领域中的报酬递增机制
皮尔森(Paul Pierson)在2005年出版的《时间中的政治》中指出,政治制度中的报酬递增现象应该是更为显著的,源于政治生活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集体行动的核心作用、使用政治权威扩大权力的可能性、政治内在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等。
国际制度作为政治制度的重要部分,是否也会出现报酬递增的现象?我们需要结合报酬递增的发生机制来进行考察。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强调非均衡状态才是经济的常态,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技术演进中报酬递增的发生机制,即大规模启动或固定成本(large set-up or fixed costs)、协调效应(coordination effects)、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s)和适应性预期(adaptive expectations)。在上述机制的作用下,某项技术一旦获得了初始优势,就很容易将这种优势一直保持下去,从而形成技术锁定,并将其他技术淘汰出局。诺斯指出制度变迁中也存在着自我增强和报酬递增现象,认为“阿瑟的所有四个自我增强机制是适用(于制度分析)的”。那么,这四种机制是不是分别会作用于国际制度领域中呢?
第一种机制是大规模启动和固定成本。我的判断是,它在国际制度中不是影响制度变迁的主要因素。因为相对于国际制度给国家带来的主权成本,国际制度本身的创立和运行成本并非大国创立的主要顾虑,大国基于安全或权力的考虑,对启动或固定成本的容忍程度非常高,即使不得不付出这样的成本,只要能够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的初始优势,这种付出就是值得的。
第二种机制即协调效应主要是表现在制度的互补性上。在国际制度领域中,某一国际制度的主导者可以通过制度互补性来诱导其他制度的建立,或者通过一揽子协定这样的战术性联系,将制度约束从本议题外溢到其他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协调效应是作用于国际制度领域的。
第三种机制即学习效应是否起作用,主要取决于这一领域的知识是显性知识还是默会知识。由于制度运作有复杂性和专业知识,往往需要默会知识和显性知识间的协调,这就使得知识接受者在学习制度如何运作的过程中,形成了与特定制度相联系的专用型资产。制度作为一种离散的社会生态,它会鼓励行为体投资于专门的技能,在制度所提供的结构中深化与其他行为体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讲,学习效应是作用于国际制度领域的。
第四种机制是适应性预期,也就是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ed prophecy)。这种机制是否起作用,主要取决于这一领域的知识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制度具有稳定性的初始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作用会有所转变。制度在最初影响参与者感知世界的方式,而后则进一步影响参与者对世界应该如何运作的看法。国际制度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者的共有信念。国际制度既可以作为焦点来汇聚参与的预期,使它们无意偏离现有的平衡,也可以发挥正当化的作用来塑造参与者的身份,使他们主动遵守国际秩序。
因此,报酬递增四种机制中,至少有三种机制作用于国际制度领域。在协调效应、学习效应和适应预期的作用下,大国在国际制度创设的初始优势就很有可能转化为长期优势。因此,报酬递增会使大国围绕国际制度创设的初始优势展开激烈竞争,当旧的国际秩序崩溃或新的国际议题出现的时候,大国会尽力把自己的偏好反映为新的国际制度设计,从而通过制度设计锁定对自己有利的制度结构。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报酬递增的现实案例
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案例可以用来说明上述原理。一个案例是英美在40年代围绕着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竞争。这个竞争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凯恩斯计划和怀特计划之间的竞争,当然是以怀特计划的胜利而告终。之所以英美在这个领域竞争,是因为其符合报酬递增的三种机制:第一是协调效应,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涉及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多个制度领域,这就意味着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会产生广泛的外溢效应,美国由此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并且主导国际贸易制度谈判;第二是学习效应,国际收支平衡的调节是金本位瓦解后出现的新议题,两种方案的较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全新知识供给的竞争过程,怀特计划胜出后,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制度安排、专业技能和程序性的知识就逐渐生成专用性资产;第三是适应性预期,布雷顿森林会议被视为“美元的加冕礼”,美国倡导的多边主义成为指导战后国际秩序的最重要的原则。这个案例是大国间国际制度竞争的一个源头,尽管直到冷战结束后,国际制度竞争才成为大国竞争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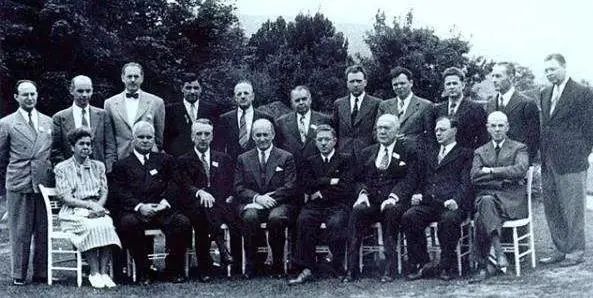
确立美元霸权的布雷顿森林会议
(图源:网络)
今天,一个比较重要的案例是美欧在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竞争。在投资仲裁的机制上,美国采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模式,欧盟则提出常设仲裁模式。从协调效应、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这三个机制来看,这个领域会发生显著的报酬递增效应,所以国际投资仲裁机制也成为美欧之间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哪一个模式占据先机、脱颖而出,得到更多国家的追随,哪个国家就可能在全球投资治理机制中占据主导地位。

2018年美墨加协议签字仪式(图源:纽约时报)
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后来者”,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参与国际经济制度。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制度的历程可以划分成四或五个阶段: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IMF和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以此为起点中国开始参与国际经济制度;到了1991年加入APEC之后,中国进一步参与国际经济制度;2001年加入WTO后,中国全面参与国际经济制度;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创造性地构建新的国际经济制度,比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投行;2017年之后,我们维护和创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至于2017年之后是不是一个新的阶段,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至少2008年之后,中国如何创设新的国际制度开始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面对当下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的危机,特别是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治理上的挑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亟待改革。随着一系列新兴议题的出现,中国有可能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气候变化、新能源等新的议题领域的规则制定上获得先发优势,也就是常被提到的“换道超车”,从而塑造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
作者田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比较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世界政治研究》主编,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免责声明:本文所阐述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立场,不代表大湾区评论或IIA机构立场。
*原创声明:本文版权归微信订阅号“大湾区评论”所有,未经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转载、复制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本文部分或全部内容,侵权必究。
GBA Review 新传媒










